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下的社会映像
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是一本特殊背景下写就的书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,美国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日本,以便制定出战后对日本的政策,由军方资助学者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,《菊与刀》便是其成果之一。这本书从另一个视角细致地观察、研究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。据介绍,日本学者并不同意书中的观点,但是,日本仍然于 1951年将此书列入了《日本教养文库》,至1963年在日本重印了36次,可见日本人对它的重视,以及此书在日本的流传之广。其实,这一做法本身,便证明了书中所提出的日本人“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”的观点。在这一点上,日本人对待外来评论的态度是与我们不大相同的,典型的例子是,1972年我们曾邀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了一部记录片《中国》,但拍成之后不但不允许在中国放映,还对其公开批判了一通,直到32年后普通观众才能看到这部片子。最近,我通过网络看过这部片子后,并没有看出什么“恶意污蔑社会主义中国”的地方,不过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那时中国普通群众的生活状态和风土人情。
《菊与刀》在国内出版之后,同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,一些读书人甚至评论说,不读此书枉为中国人。此书之所以在文化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,我想,原因大概有二,其一是我们现在也正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亟须深入地了解日本,了解那个曾经对我们这个民族犯下了不可忘记的罪恶的国家;其二,从文化归属上讲,日本与我们一样,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,在文化成分上有些许相同之处,读一读这本书,多少也可以从中窥见一点我们的影子。
抛开书中的其它观点不说,从文化分析论上讲,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所提出的“罪感文化”与“耻感文化”。
所谓“罪感文化”,就是“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,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 ‘罪感文化’。”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,意思就是在“罪感文化”社会中,人如果违背了那个“绝对的道德标准”就会感到是有罪的。这一点,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“天主教”中的“人生来是有罪”的说法略有不同。但也还是能够从“罪感文化”的定义中得到解释,因为人类的始祖——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“绝对的道德标准”,听信了蛇的谗言,偷吃了禁果,犯下了罪恶,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。
然而,什么是“耻感文化”呢?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,只是说“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。”根据本尼迪克特对“耻感文化” 零零碎碎的介绍,我想,所谓“耻感文化”,就是也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,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。相对于“罪感文化”,“耻感文化”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罢了。
由此,现在我们便可以来对比这两种文化的异同,并以此来观照分别由这两种文化所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了。
没有疑问的是,不论是“罪感文化”还是“耻感文化”,它们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,那就是为的都是“劝人向善”,并最终建立一个“善”的社会。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,一旦违背了那个“道德标准”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,会有一种懊悔、羞耻和罪恶的感觉,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,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。
但是,这两种文化在“导人以善”的作用机制上,却又有着重大的不同。
在“罪感文化”中,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“绝对的道德标准”,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, “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,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,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。”也就是说,“罪感文化”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,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,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。对此,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《罪与罚》中,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。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,杀死那个年迈的,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,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,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。然而,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,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,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,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。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,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,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。他想尽一切方法,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,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,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。最后,他只好去自首,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,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。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,我们感到了“罪感文化”的力量。
相比之下,“耻感文化”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。“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。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,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。无论哪一种,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。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,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。”⑤这也就是说,“耻感文化”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,因此,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。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,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“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”,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。相反,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,“耻感文化”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“罪感文化”中的那样大。
由于这种导向机制的不同,所以,在“罪感文化”和“耻感文化”之下,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社会景象。
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,在“罪感文化”下,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。在拙作《忏悔的土壤》中我曾说: “忏悔是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,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,是彻底、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,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。”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,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。与此相对应,在“罪感文化”中,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、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。二战之后,德国的政治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,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,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。反过来,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,又对主动、自觉、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,从而强化了“罪感文化”的力量。
在“耻感文化”中,要想使人们对过错保持羞耻感,则必须不断地保持住一种舆论的压力,形成一种“宣扬过错”的舆论氛围,使人感到周围有着无形而又无限的压力,觉得背后老是有人在看着自己,议论着自己,甚至用自己的过错或恶行在教育着别人,让他人引以为戒,在明里或暗里把他钉在了“耻辱柱”上,使其活着感到不安,即使死了也是“遗臭万年”。由此,我们便不难理解社会生活中的“长舌妇”现象了。当然,这里并非是在歧视女性,所谓“长舌妇”,说的是爱在背后说三道四、拨弄是非、传播小话的人。这种人,有女人,也有男人。从“耻感文化”的角度上讲,这不但不是一种恶行,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,在某种程度上说,它还是“耻感文化”所需要的外部舆论压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耻感文化” 中需要这种人在明里暗里议论他人的短长,从而制造出“耻感”的压力来。所以,说一个人是“长舌妇”,并不让感到十分地厌恶,只是有一点反感而已,有些人甚至还喜欢它。不然,一种“恶俗”决不会历千年而依然活跃得很。当然,提起“长舌妇”,有的人可能有点儿厌恶,但这大多是在“长舌妇”议论到自己的头上才有的感觉,或者这种感觉才更强烈一些。
相反,一些人如果听到“长舌妇”在议论别人的“丑行、恶行、短处、不是”时,则听得津津有味,甚至暗地里感到自己比那个被议论的人在“道德”上高尚与纯粹得多。因此,在“耻感文化”中,人们是很难有个人隐私的,“耻感文化”很容易派生出“窥视他人隐私”的文化兴趣来的。
分析了“罪感文化”和“耻感文化”的特点和作用机制之后,我们不妨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种文化的另一面,或者说,看一下这两种文化在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时,是否存有先天性的漏洞。
从理论上分析,注重内省、内动的“罪感文化”,由于它以内因为主,应该说,只要这种文化发生作用,其运行机制是比较周密的,没有多大的漏洞可寻。一个人只要犯下“罪恶”,违背了那个“绝对的道德标准”,无须外力的参与,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。只要“罪感文化”这台机器运行起来,便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出来。而“耻感文化”便不同,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,需要外力的启动,这就给人留下了“脱耻”的暗道。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,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,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。
因此,乖巧的人,做下了恶事,有了恶行之后,首先想到的是“千万不能让人知道”,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、隐藏、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、恶行。一般说来,在“耻感文化”社会中,媒体舆论是很难开展“负面报道”的,原因就在于虽然这种文化需要舆论压力来促成耻感,但由于这种耻感是外加的,而不是内生的,所以人们总是愿意用相应的手段来逃脱这种耻感。近年来,“神道文化”盛行,各地庙宇香火旺盛,进庙烧香拜佛者络绎不绝,许多人家中的内室里还供有佛龛,但这些都不是用来忏悔的,而是用来祈福求运的。因为一些人做起事来是讲究“神不知鬼不觉”的。“脱耻”的另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,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,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。与德国人相比,在对待二战罪行上,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,更不以为此而感到耻辱,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。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,篡改历史教课书,隐瞒历史真相,对别人举出来的铁证视而不见,可以说,这正是“耻感文化”本身给他们开出的后洞。为了弥补“耻感文化”本身的这一不足,便有了“要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”之类的警语,而且把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的“四知”官员奉为守官德的楷模,历久诵扬。但想一想,这种方法则又流于 “罪感文化”的套路中去了。
于是,在“耻感文化”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,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,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“耻感文化”的另一面,也就是“脱耻”的通道。因为,即使是惯常在“月黑风高夜”杀人越货的“黑老大”,只要他行事机密,做得神不知鬼不觉,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,也会运用强力“封了口”,那么,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“道德完人”。所以,我担心这种对付“耻感文化”的法子发展到极致,“耻感文化”也就可能只剩下了一面好看的旗子。原因在于,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人们,只要达成一个集体的协议,“你不说我,我也不说你”,把外部的舆论压力全部消解掉,那岂不是很容易达到“耻感文化”中所要求的那个“道德标准”么,如此,“人人皆圣贤”的社会也就来到了眼前。
Subscribe to:
Post Comments (Atom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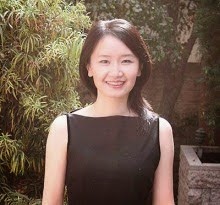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